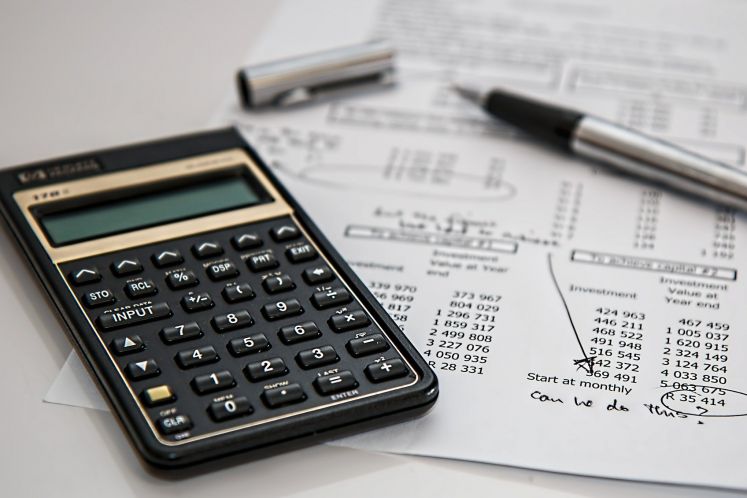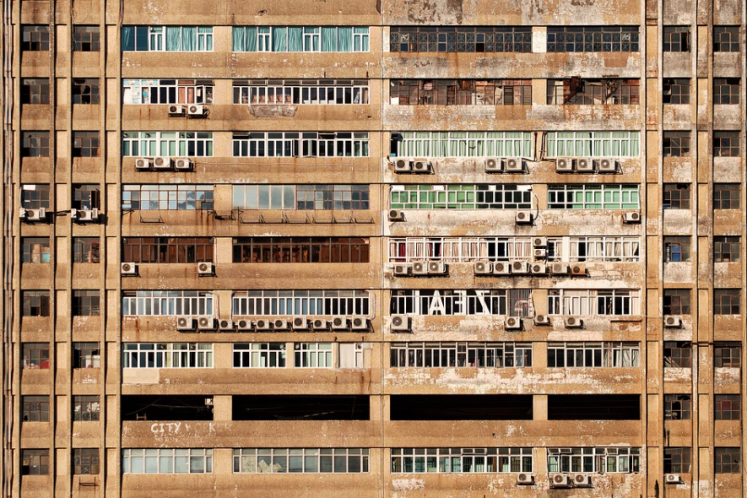作者:薯條三兄弟
來源:大隊長金融(ID:captain_financial)
01 /
跨年的晚上,酒酣耳熱之際,一群金融民工的朋友圈又被一則新聞刷屏了。在滿目的跨年party照片之間,星星點點不斷出現以“重磅!”、“突發!”、“定了!”等金融圈常用詞作為標題的文章。
打開一看,哦,原來是醞釀了3年之久的《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條例”)公開征求意見了。
02 /
條例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第11條:“(七類)地方金融組織應當堅持服務本地原則,在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區域范圍內經營業務,原則上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業務。”
哪七類?第9條定義:“本條例所稱地方金融組織,是指依法設立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授權省級人民政府監督管理的從事地方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
03 /
看到這個文的時候,我的內心是平靜的。平靜到我都認為對于這個文本身的文義沒什么好解讀——因為大邏輯已經,且早就非常清晰了。
大邏輯是什么?一句話——監管套利長不了。
總結一下中國金融市場過去幾十年的監管套利,大路徑無非是利用三對矛盾:
第一對是橫向矛盾,即利用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監管邏輯不對稱——你有你的通道,我有我的牌照,問我怎么開搞,只需層層嵌套。
于是乎就有了信托套資管加理財、合格投資者互聯網大拆小、各種計劃滿天飛、收益權受益權傻傻分不清楚——這正是這五年來被以大一統資管新規為代表的監管組合拳重磅打擊的。
第二對是縱向矛盾,即利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監管邏輯不對稱——你發你的中央牌、我發我的地方牌,地方加個互聯網,全國展業還是香。
第三對還是橫向矛盾,即利用不同地方之間的監管邏輯不對稱——你做你的金融創新、我做我的政策洼地,招商引資KPI,全靠牌照發起來。
于是乎就有了廣東的互聯網小貸、地級市縣級市也能批出一個的地方金交所、當半個金融機構來用的融擔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以及數千家更加狂野的連地方牌照都沒有的裸奔型保理公司——條例正是打擊利用縱向矛盾進行監管套利的旗幟鮮明的檄文。
所以,看條例最好不要單獨看,要結合資管新規一起看,結合以前發過的其他文和做過的其他事一起看。
04 /
資管新規的邏輯,三句話就說明白了:
第一句,統一標準;第二句,實質重于形式;第三句,穿透式監管。
那么條例的邏輯,其實三句話也能說明白:
第一句,還是統一標準;第二句,中央規劃、地方擔責;第三句,全國業務中央批,地方業務地方批。
簡單來說,資管新規和條例,都是原則性規定大于細節性規定,或者說,主要體現的是邏輯而不是技術的文件。所以,你不管怎么看條文,條文都不會大于或不同于他們的基本邏輯。
接下來我們分別講講這三條邏輯。
05 /
為什么首先都是強調統一標準?因為統一標準是監管套利的大敵。監管套利其實就一招——找洼地。橫向的,哪個通道能投底層我找哪個放最下面,哪個通道能吸頂層我找哪個放最上面。縱向的,哪個地方同樣功能的牌照要求最低,我去哪里設。
未來的趨勢就是全國一盤棋——一律拉平,沒有洼地了。結構融資從高等數學變成了小學數學,憑感覺大概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這次就明確了有哪些牌照、誰來發、有什么條件、有什么功能——這些標準全部統一了。
所以才會有所謂:
“地方金融組織指依法設立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授權省級人民政府監督管理的從事地方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強調地方金融組織持牌經營,設立區域性股權市場應當經省級人民政府公示,并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備案,設立其他地方金融組織應經省級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并頒發經營許可證。地方金融組織應當服務本地,原則上不得跨省開展業務。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業務的規則由國務院或授權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定。”1
某一地方的地方政府很難再創造出一張價值大幾千萬上億能被當成香餑餑并購標的的金融牌照了。
06 /
后面兩句就比較特別了。
首先,“中央規劃、地方擔責”是啥意思呢?
就是有哪些牌照、誰來發、有什么條件、有什么功能,這四件大事,制定權是中央的。你地方政府不能自己發明創造牌照,只能在中央制定的框架下按套路出牌。
按套路出牌,牌還是你自己出。所以中央規劃好了以后,地方還是“誰審批、誰監管、誰擔責”2,其實核心也就是擔責。也就是說對這些牌照平時具體干活兒的還是你地方,出了風險你也別轉嫁中央。
其次,關于“全國業務中央批,地方業務地方批”這事兒。
簡單來說就是,地方無論怎么批,都不能讓這個牌照的權限超出地方的范圍。
那么這里面就有兩條路徑了:
要么,你找中央給你批,一把你就能全國展業。
這就是為什么“地方金融組織跨省開展業務的規則由國務院或授權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定”。
要么,你不斷地找地方,你多做一個地方,就多找一個地方。
這就是為什么“地方金融組織在省級行政區域內設立分支機構,變更名稱或者營業場所,增加注冊資本,變更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自分支機構設立之日起或者相關事項變更之日起30日內向省級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備案”。
所以你抬頭一看,發現有些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啊,已經在全國各地設了無數分公司了。
或者,找跨省機構合作開展業務,是否也會是個選項?
07 /
在對于地方金融牌照進行監管的博弈過程中,其實邏輯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他也曾變過很多次:
比如,能不能通過提高門檻,增加要求的方法,把地方性金融牌照拉平到全國性金融牌照的標準,使得問題自然解決?
2019年10月的《關于加強商業保理企業監督管理的通知》(即大名鼎鼎的“205號文”)就不得不說是這樣的一個嘗試。
而2020年5月的《融資租賃公司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即大名鼎鼎的“22號文”)則是把這個邏輯用到了巔峰——基本上把商租公司的門檻和監管要求完全抬高到了和金租基本相同的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文件的頒布機構都是銀保監會,且這兩個文件目前都仍然現行有效。
就在2021年10月,銀保監會官網也仍在政務咨詢欄目中給出這樣的口徑:“目前對融資租賃公司異地經營沒有明確監管要求。但在監管導向上,支持融資租賃企業主要服務本地、深耕本地市場。”
這是否意味著,目前不同的監管機構,對于在監管實踐中到底采用哪一種邏輯,還沒有完全達成共識?
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樣作為資管新規體系的標桿性文件,《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可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四機構聯合發布的。
08 /
實際上,從執行的角度,直到現在,205號文和22號文相關的現場檢查和清理整頓,即使在各地金融監管部門借助外包力量的情況下,也并未完全完成——涉及面實在是太廣了,例如就在本文撰寫的當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又再次更新非正常經營商業保理公司名單。
所以,當然也是需要過渡期的,正如條例第38條所規定:“本條例施行前設立的地方金融組織,不符合本條例規定的,應當在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期限內達到規定條件;已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業務的,由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明確過渡期安排,實現平穩過渡;逾期仍不符合本條例規定的,不得開展本條例規定的相關地方金融業務。”
我們還是跟資管新規比比,資管新規的過渡期,可是很明確的:“過渡期為本意見發布之日起至2020年底”。
相比之下,這個過渡期安排,好像顯得從容不迫了。
不僅如此,資管新規還對過渡期進行了延長,并談到了主要考慮:
“一是統籌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延長過渡期1年,更多期限較長的存量資產可自然到期,有助于避免存量資產集中處置對金融機構帶來的壓力。二是過渡期也不宜延長過多。過渡期安排的初衷是確保資管業務順利轉型,實現老產品向新產品的平穩過渡。將過渡期延長1年,可以鼓勵金融機構“跳起來摘桃子”,在對沖疫情影響的同時,推動金融機構早整改、早轉型。三是最大化政策效用。過渡期延長1年,能夠較好統籌存量業務整改和創新業務發展的關系,通過資管業務的轉型升級,帶動存量資產的規范整改。”
其實,過渡期本就是個玄學,在地方金融監管里,甚至可能只是個口號。
從P2P、到金交所、到保理公司、再到融資租賃公司,在地方金融監管的歷史里,就沒有哪一次過渡期按期執行過。
比如說,條例32條提到了“對地方各類交易場所的監督管理”——說實在的,金交所的兄弟們看到可能也早就麻木了。畢竟早在2011年的38號文和2012年的37號文時代就開始清理整頓了——2011年38號文提出的整改方案上報期限還是“2011年12月底”。
后來的故事就不多說了,哦不,就說一個:
2019年初的時候,清整聯辦還發了一個35號文,我就說一下這文的標題:
“三年攻堅戰期間地方交易場所清理整頓有關問題的通知”。
09 /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條文:“省級人民政府履行對地方金融組織的監督管理和風險處置職責,承擔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屬地責任,督促各類股東履行補充資本的義務,對省級行政區域內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負總責。”
而在條例中,5%以上股權的股東即屬于變更需要批準的主要股東。這意味著:凡超過5%的股東,都可能實際上承擔資本補充義務,也可以理解為是某種程度的連帶信用責任。這是以往任何規定所不曾有過的。
在這里,我們同時也把《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管條例》的第17條貼出來,大家可以結合上面的條款,細細品味有沒有隱藏的邏輯:“地方金融組織的股東依照法律規定以其認繳的出資額或者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地方金融組織承擔責任。
地方金融組織可以建立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承擔剩余風險責任的制度安排,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可以出具書面承諾,在地方金融組織解散或者不再經營相關金融業務后,承擔地方金融組織的未清償債務。地方金融組織可以將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是否承諾承擔剩余風險責任的情況向社會公示。”
10 /
條例中還有一塊比較核心的內容,可以總結為執法權的明確和罰則的細化。
地方監管部門原來的執法權到底包括哪些具體內容?一直以來是長期缺位的,地方監管機關的“無權”也由此成為了地方監管機關放任市場的借口。
新規給出了全套的武器。
從檢查,到執法,再到處罰,地方金融監管機關具備了不亞于一行兩會的行政權力,現場檢查、非現場檢查、查閱、復制、詢問一應俱全,整個第四章再滿滿地碼上罰則——對非法金融活動的處罰、未經審批、備案的處罰、未報告重大風險事件的處罰、不配合監督管理的處罰、為開展統計工作的處罰、對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處罰等。
從此時候,“想管管不了”再也無法成為托詞。
11 /
說了那么多,千言萬語匯成幾句話:
第一是要讀懂邏輯:只要不違反邏輯,辦法總是有的。要是違反邏輯,辦法總有一天也不再是辦法。
第二是要看清大勢:現在怎么樣不重要,總有一天總會怎么樣才重要。
第三是要理解灰度:任何一個法規,只要是觸及大范圍業務和長期矛盾的,灰度執行往往都會是實踐中的方向。
第四是要明白時局:央地博弈不是只在金融監管領域才有的問題,因此也很難期待中央一紙文件就能徹底扭轉現狀。狼來過不止一次了,邊走邊看,放輕松。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題圖來自 Pexels,基于 CC0 協議
本文由“大隊長金融”投稿資產界,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謝謝!




 大隊長金融
大隊長金融